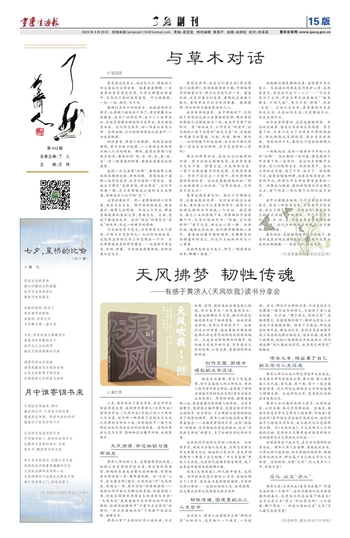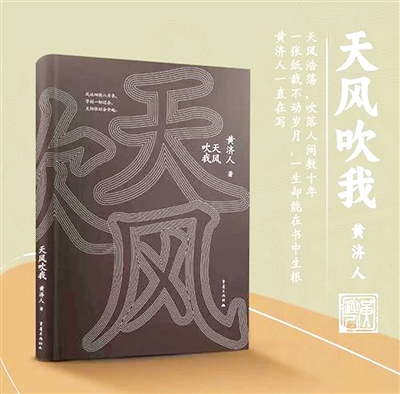◎ 熊生萍
八月,有幸参加了著名作家、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主席、我的师兄黄济人《天风吹我》读书分享会。《天风吹我》是他以近八十载的人生为墨,创作的一部承载了家国变迁与文人风骨的自传体小说,深情绘就了一幅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壮阔画卷。这场分享会正是与文学、坚韧和过往展开对话,我收获颇丰。
天风溯源:命运枷锁与使命微光
黄济人师兄的人生,自带着厚重的底色,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出身,曾是国民党高官,特殊的家庭成分像沉重的枷锁,使得他每向前迈进一步,都布满荆棘。而“天风”二字,恰与龚自珍《湘月·天风吹我》中“天风吹我,堕湖山一角,果然清丽”的意境相契——他便如词中被天风拂过的灵魂,纵落困境一角,仍能在困顿里寻得生长的清丽与力量!“天风吹我”更藏着他半生对命运的叩问与挣脱,仿若郑板桥诗中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劲竹,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于荆棘中深深扎根、顽强生长。
黄济人曾下乡到四川内江威远县,当过知青、老师,因家庭成分遭受他人轻视,却从未有过一丝堕落的念头。在威远的那段岁月里,破旧的泥巴墙房屋见证了他的青春。他说老房未拆时,还曾打算将其买下。这份对过往的回望,饱含着他对那段满是挣扎却也孕育韧性时光的深深缅怀。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,他似被天风选中的行者,背负着对文字的使命,以笔为舟,誓要挣脱命运的泥沼。
创作突围:困境中崛起的文学远征
饱受生活磨砺,等来了恢复高考,好不容易进入内江师院后,黄济人想用写作改变命运,后来有了那部名动海内外的纪实文学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。厚重的书稿,凝聚着他的心血,更浸透着同窗间暖人的情谊。当时书稿繁多,整理装订格外费力,是寝室的同学们主动搭手、合力帮忙,才让那摞沉甸甸的稿纸有了规整的模样。黄济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总带着感念——在物资紧俏的年月,这份“搭把手”的情分,是撑着他往前走的暖光,也让“用笔改变命运”的誓言,多了份被伙伴托举的力量。
这段经历是他对文学初心的践行。从知青岁月,到成为全国人大代表,与陈忠实等文学大家围坐交流,他始终以笔为刃,在文学领域劈开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“中文系基因”里的人文底色,也在时代浪潮里愈发醇厚,成了我等后辈望得见的精神灯塔。
谈及《天风吹我》,师兄眼中有光,也有憾。创作时他反复打磨的21万字,出版时删去了6万字,虽未成为最理想的模样,可书终究得以面世——这恰如他的人生,纵有遗憾,也总要让生命之花朝着光的方向开。
韧性传魂:困境里的向上人生哲学
分享会上,黄济人说困境中总有“神秘力量”拉他前行,或是他人一个微笑、一句鼓励。其实,哪是什么神秘力量,不过是他自己先攒着一股不放弃的劲儿,才接住了旁人递来的暖。孔子说:“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”,在物质匮乏、处境艰难环境下,精神支撑与人文温度才是破局密钥。他虽下乡威远,却成先进知青代表、被选为队长,靠的正是在逆境中向上向善的选择让他发光,迎来机遇、迎来贵人的帮扶;把他人的质疑化作奋进动力,用行动诠释“别人朝我扔泥巴,我用泥巴种荷花”的豁达。
传承之幸:辟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与人生征途
黄济人师兄从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走出,成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,第七届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九届、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,内江师院也因他在文学传承版图上熠熠生辉。这是师院之幸,更是我们这些后辈校友之光。
黄济人如文脉传承的火炬手,从师院出发,以笔为翼,载文学舟楫远航。在他家,看他与陈忠实等文艺界名人的合影,听他讲《重庆谈判》在中国台湾出版引发的反响,他的作品早已超越文学本身,成为时代与历史的鲜活注脚。而《天风吹我》,不光是师兄人生际遇的反映,更有时代交替更迭时各类环境生态的投影与文艺界的风云际会……
这场分享会于我而言,是文学与精神的双重洗礼。黄济人用人生诠释:困境是试金石,只要如劲竹般坚韧、似天风般怀揣使命,便能在命运洪流中,辟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与人生征途。这份韧性,当随“天风”,吹入更多人心中,传承不息!
后记:以文“济人”
黄济人在《天风吹我》扉页为我题了“热爱生活的每一片绿叶”,这些字瞬间幻化为绿意盎然的春天,也更似天风过后落下的星光!这不正是以文“济人”印证其名吗?心头有暖,脚下有光——热爱与坚韧当是“天风”予人最实在的力量!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永川中学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