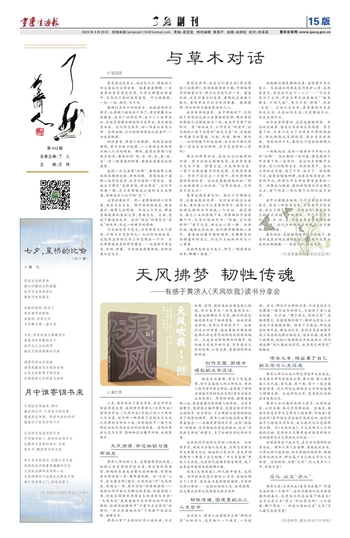◎ 张凤鸣
晨光漫过巴岳山,淌过巴川河,将我的小阳台染成淡淡的金色。细看盆盆罐罐,一些盆里的青苔颜色变深,不管不顾蔓延到盆外,自然比干枯时候有意思。叶上的露珠,一粒,一粒,相同,又不同。
植物们来自不同的地方。虬枝盘曲的金弹子,从黄桷门搬回家十年了;旁边舒展自如的银杏,来自广汉的花市;至于小小的罗汉松,应该是某棵古树的种子发芽后,原生苗培育而成。它们形态各异,却一同在此安身立命。光阴流转,它们的根须深深扎进盆中,一如我在铜梁。
初识盆景,带着几分执拗。铝线在指间缠绕,剪刀在枝头起落,一心想将自然的野性纳入人为的规制。那时,最常去黄桷门请教左会长,看他如何“起,承,转,合,落,结,走”,将一株普通的树苗,塑造成意蕴深远的盆景。
直到一次为盆景“松绑”,看到枝条上被铝线深勒的疤痕,特别刺眼。再望向数十盆精心培育的盆景,我忽然感到一阵窒息。想起庄子那句“凫胫虽短,续之则忧”,它们中的每一株,是不是都被我以爱的名义束缚着,扭曲成世人认可的“美”?
也曾试着放手。将一盆黄杨移到小院角落,任其自在生长。刚开始新枝疯长,绿意盎然,颇有几分野趣。然而几个月后,那盆黄杨枝条就杂乱无章,意趣全无。自由,竟成了散漫的失序。我对“病态”的隐忧与“杂乱”的厌弃,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完全放任等于荒芜,过度修剪又近于摧残,平衡点究竟在何处?如此纠结的后果,是想写盆景的文章三年没憋出一个字。目光常常被盆里的野草攫住——从缝隙中冒出来,纤细,舒展。不怕被我连根拔起,始终向着天空生长。
想想这些年,我在它们旁边读《草木缘情》《菜根谭》,煮麻麻辣辣的火锅,听掷地有声的铜梁方言,偶尔大声武气学一句。最喜欢的,还是对着它们发呆,看蚂蚁沿着枝干爬行,看新芽在不知不觉间舒展。植物静穆,却比任何言语更能安抚人心。
我重新审视盆景。在夕照映衬下,它的枝干呈现出巴岳山岩壁般的色泽,那些曾经的勒痕已与树皮融为一体,成为岁月留下的印记。在“缩地成寸,小中见大”的盆中,让见到的人除了具象的“枝无寸直”外,还能把世间诸多的聚散,巧拙,残损,掩映,留白……如呼吸般平和地接纳,在天地万物之间搭一座来去自如的桥,这才是盆景的心意吧?
每次的修剪时光,是我与它们独有的对话。剪刀在指尖微微发亮,我却常悬着手久久不落。修剪之道,亦是取舍之道。一剪下去便是诸多旧时光啊,总要思量再三。有时只是拈去一片枯叶,有时稍稍调整铝线的松紧。这让我想起妈妈的话:“待人接物要留三分余地。”与草木相处,又何尝不是如此?
最享受雨后看它们。每片叶子都被洗净,泛着油亮的光泽。这时我就旋过去旋过来,看水珠从叶尖滚落的样子,看果子上的绒毛被雨水冲刷成一个方向。若是周末,楼上小女孩会跑下来,用稚嫩的手指轻触叶片,又急忙缩回手问:“阿姨,它们会疼吗?”童言无忌,却让我心里一颤。我告诉她,植物也会说话,我们要用眼睛和心来听。看着她似懂非懂的模样,仿佛看见初来铜梁时的自己,对这片土地既好奇又小心翼翼。
遂拍照发给远方友人,附言:“铜梁雨后初霁,聊赠一枝春。”
闲翻微信朋友圈的记录,盆景图片变化很小。天南海北的朋友笑问养护心得,我思索良久,真还说不出个一二三——“不过是在方寸之间,学会与草木温柔相处”“枝里精生,叶间气润”,重点不在“修剪”,而在“生发”。正如人生在世,最重要的不是在何处生活,而是如何生活;不是塑造什么,而是发现什么。
如今我再修剪时,总会先静静观察。手指抚过枝条,感受它内在的生长趋势。剪子落下时,不再只是为了实现某个预设的造型,铝线缠绕也变得轻柔,留出生长的余地。有时端详半天,最终也只是轻轻理顺几根杂枝。
一场秋雨后,我给一株养护多年的六月雪“松绑”。指尖触到一处旧痕,像是摸到了岁月留下的一道契约。我这双手曾赋予它形状,它以沉默的生长,告诉我尊严。我们之间的这笔账,算了十年,扯平了。铝线取下后,枝条会缓缓回弹,疤痕会慢慢愈合,所有的印记,终将化作生命故事里温柔的一笔。就像我与铜梁,最初的隔阂与不适都已淡去,留下的是一份扎根于此的从容与安然。
盆中之境教会我的,不只是莳花弄草的技艺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:在约束中寻找自由,在方寸间见天地。万物生长,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生命的奥秘。早已不介意它们的横、斜、卧、悬,书桌放置盆景的高度贴合“平视”,我们正好做彼此的镜子:壮不痴肥,瘦不残废。
暮色四合,我轻轻抚摸罗汉松的枝干,感受时光在指间流淌的痕迹,感受枝叶花果与我的如期相遇——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。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