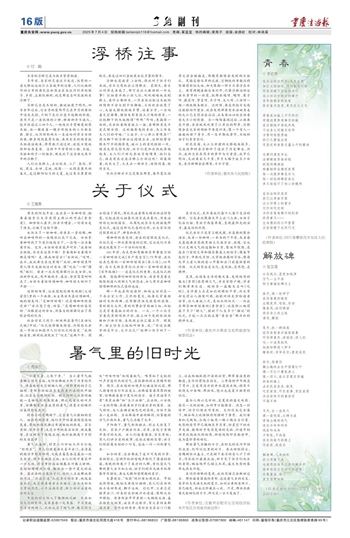◎ 周基云
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” 当小暑节气踮着脚尖悄然来临,太阳仿佛被点燃了内里的烈火,将毒辣的光芒倾洒人间。田野里的稻子已抽穗,青郁郁的稻浪在裹挟着热浪的风中翻涌,似是在与骄阳较劲。树上的蝉儿从黎明破晓一直嘶鸣到夜幕低垂,那此起彼伏的叫声里,仿佛都裹挟着滚烫的暑气,将夏日的燥热渲染得愈发浓烈。
村西头的老槐树下,总坐着几位歇晌的老人。斑驳的树荫里,他们手中的蒲扇慢悠悠地晃着,带起的微风拂过布满皱纹的脸庞。家长里短、陈年旧事,或是今年的农活安排、收成展望,在这树荫下缓缓流淌,编织成独属于乡村的生活篇章。
暑气正盛时,村里人巧妙地与烈日打起 “时间差”。男人们披着满天星斗出门,在清晨的微凉中躬身田间,又赶在暮色吞没最后一丝天光前,将汗水洒进土地;女人们则守着家中一方天地,将金黄的稻谷铺展在竹匾上晾晒,在坛坛罐罐间忙碌,腌制出一整个夏天的咸香。最欢快的当属孩子们,他们三五成群地奔向河边,“扑通扑通”扎进清凉的水里,溅起朵朵水花;或是跟着母亲去水塘边,在浅浅的水洼里玩泥巴,小手沾满泥浆,脸上却洋溢着纯真的笑容。
午后的村庄陷入了慵懒的沉睡。热浪如同无形的巨网,笼罩着每一处角落。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狗儿,此刻也没了精气神,蜷在阴凉处“呼哧呼哧”地喘着粗气。唯有知了尖锐的叫声穿透炽热的空气,在寂静的村庄里格外刺耳。偶尔,卖冰棍的吆喝声打破这份沉寂,那人推着的自行车后座上,冰棒箱裹着厚厚的被絮,仿佛藏着整个夏天的清凉。箱子里通常只有“香蕉冰棒”和“豆沙冰棒”,五分钱、六分钱一支的价格,承载着孩子们最朴素的渴望。运气好时,大人会掏出皱巴巴的零钱,为孩子换来一支冰棍。当冰棒箱开启的瞬间,白雾般的凉气扑面而来,暑气已消散了大半。
夕阳西下,暑气渐渐褪去,村庄又恢复了生机。家家户户搬出竹床、凉席,在院子里铺开乘凉的天地。女人们摇着蒲扇,家长里短;男人们讲古老的故事、谈论庄稼的长势;孩子们则提着自制的小灯笼,追逐一闪一闪的萤火虫……
如今回首,这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旧梦。再回村庄,空调外机的嗡鸣声取代了蒲扇的轻摇,夜晚的街巷少了乘凉的人群,曾经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不知去向,孩子们的目光被手机屏幕牢牢锁住,再也无暇仰望璀璨的星空。
大暑前后,“双抢”的忙碌如期而至。早稻成熟待收,晚稻又要赶忙插秧,农人们在田间地头来回奔波,脚不沾地。记忆中,父亲总是摸黑出门,归来时衣衫被汗水浸透,像刚从水中捞起。母亲则会早早煮好一大锅绿豆汤,盛在粗瓷大碗里,放在井边晾凉,等父亲回来解渴消暑。劳作后的母亲,有时会坐在后门门槛上,让我给她抓挠汗湿的后背,那带着温度的触感,至今仍萦绕在指尖。三哥每到中午便没了胃口,总爱用清凉的井水浸泡米饭,稍等片刻便大口吞咽,那滋味,想必也是夏日独有的记忆。
最令人难以忘怀的,是夏夜的露天电影。每月一次的放映,如同节日般隆重。消息一经传开,孩子们便欢呼雀跃。太阳还未完全落下,晒谷场上就陆陆续续摆好了条凳。我们匆匆扒完晚饭,扛起小板凳一路小跑去占位置。电影的情节早已模糊在岁月里,但星空下的欢声笑语、散场时手电筒晃动的光柱、归途中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,却深深烙印在脑海中,成为最珍贵的回忆。
那些暑气蒸腾的日子,在时光的长河中悄然流逝,化作记忆里的碎片。再次回到村庄,老槐树依旧矗立,只是树下乘凉的老人少了许多;河水依旧潺潺流淌,却不见了孩子们戏水的身影;晒谷场早已铺上水泥,露天电影的幕布也再未升起。
在闷热难眠的夏夜,我的思绪总会飘回过去。那些摇着蒲扇的身影、追逐萤火虫的欢笑、简单而又充满生机的夏日,如同泛黄的老照片,虽已褪色,却永远珍藏在心底。只是,那些承载着无数回忆的日子,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(作者单位: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高刘派出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