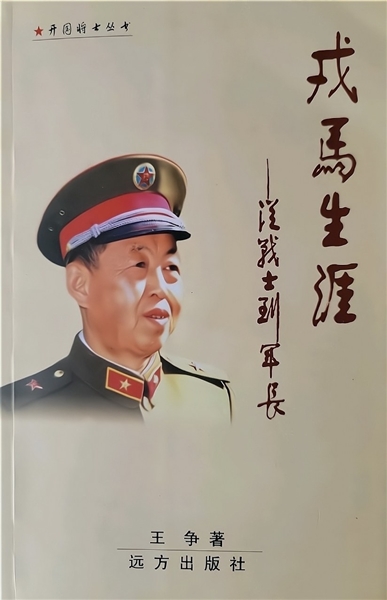◎ 李耀国
我的老首长王争的女儿西西寄来她父亲出版的回忆录《戎马生涯》,记述了王争从战士到军长的革命经历,使我激动万分。虽然我参军时,王争就是师长,在新兵心目中,师长已是很大的官了,我们只能仰视他。后来我成了老兵,被调到师政治部工作,由于王争是军事主官,不属于他直接领导,因此工作上少有接触,偶尔在路上碰到他,他也只是随意问问我最近在写什么,我回答后他点点头就离开了,并不和我深谈,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。不久后他调到军部,我也复员返乡,从此失去联系。看了他的回忆录我才知道,除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那部分战斗经历外,他在和平时期领导的战备训练,我都亲历过,读来十分亲切,和他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,便像珍珠串起来。
我刚到部队时分到炮兵团,和师部仅一墙之隔。那时我很喜欢文学,空闲时爱去图书馆,我意外地发现,师长也常来这里,我有些惊讶,作为一名军事主官,他也会对文学有兴趣?我还注意到,他借阅的书籍中竟有外国名著。我知道他们那一代是在战争时期参军的,多数没有上过学,或者文化程度很低。我也是从回忆录里才知,王争在家乡念过小学,抗日战争爆发不久,年仅13岁的他,便在山西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“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”,后来随部队从北打到南,身经百战,在淮海战役中,他任营长,带领部队直插敌人军部,打乱了敌军部署,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,被评为战斗英雄。
在和平时期,部队也要居安思危,随时准备打仗。我师一直担任总参战备值班师任务,根据山岳丛林作战特点强化训练,被中央军委命名为“丛林猛虎”称号。王师长对部队训练提出“从严、从难、从实战”要求,一切从实战训练部队。一次,在观摩炮团榴炮营实弹打靶时,有门大炮三发三中,当班长以为会受到表扬时,王师长却评了不及格。王师长指出:“你虽然三发三中,但你炮位选择不正确,没有任何掩体,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当你发射第一颗炮弹时,马上就暴露了目标,容易遭到敌方的反击。”后来,我就此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军报上。
山岳丛林作战训练的艰苦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,就连有过战争经历的部队领导,也不相信在热带丛林里行军,一个小时只能前进一公里。当他们亲身经历后才明白,原始森林长满了荆棘和藤蔓,部队每前进一步,都得靠人砍出一条路来。1965年雨季,我随全师部分连、排干部参加的为期一个月的“三无三定”(无道路、无村庄、无向导;定时、定点、定路线)训练,也被称之为“适应性生活锻炼”,由于热带雨林山高林密,后勤补给困难,但林中生长的野菜和动物可以利用,因此,探索部队在后勤补给不上的时候如何生存?便成了训练的重要课题。当我们走进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,林间雾气弥漫,光线阴森幽暗;树叶上挂满干蚂蝗,从衣领掉进脖子里,拍掉后满背是血;脚下铺着厚厚的腐败的落叶,冒出的气泡发出恶臭,许多人被中毒感染,行走艰难,还要时时提防猛兽和毒蛇的突然袭击。尽管我们带着干粮,但那是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享用,整个行军都是靠野菜和打猎为生。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艰苦的岁月,也是我最难忘最宝贵的一段经历。
训练快结束时,集训队大队长找到我,说王师长想听汇报,他和指导员走不开,要我下山汇报。我只身走出森林,来到位于中缅边境的耿马孟定坝,找到师部所在农场,在路口就碰到王师长,我向他行了个军礼,他并不答话,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,我愣在那里,不知所措。过了一会,他皱了皱眉说:“你看看你这身军装,你们在森林里,没有老百姓,穿得随便点没有关系,到了这里,老百姓多,要注意军容风纪。”我这才注意到我的军装已被荆棘划破,到处都是破洞。我有些委屈,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,想起还在森林里的战友,他们跟我一样餐风饮露,披荆斩棘,军衣也是千疮百孔。王师长似乎明白了什么,他把手搭在我肩上,声音也变得柔软起来:“别哭了,赶快到会议室汇报,总参的首长在等着。”后来,结束这次集训后,战士们回到各自连队,立刻补发了一套新军装,我感到我的眼泪并没有白流。
农场的会议室很简陋,一张方桌四面摆着长条木凳,靠壁的位置放着一些竹椅,首长们散坐在各处。天气闷热,大家都穿着衬衣,看不出军阶来,我因生性腼腆,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,难免有些紧张,甚至不敢抬头。虽然我不善于总结归纳,但我擅长讲故事,此次主动要求参加穿林训练也是为了收集素材。在丛林生活的日日夜夜,战友们为了崇高的信仰,战胜了生命极限的挑战,一个个生动的故事,像泉水一样从我的嘴里涌了出来,这些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,整个会场鸦雀无声。当总参的首长回到北京后,立即派出八一电影厂的摄制组来到这里拍摄军教片《丛林生活》,我也作为撰稿人参加了这项工作。王师长对我的汇报非常满意,晚饭后特意要我陪他散步。他向我谈到,在淮海战役时,著名军旅作家寒风到前线采访,和他蹲在一个战壕里。后来寒风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小说《党和生命》,表现了在革命战争中对党的忠诚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,使他感动不已,使他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巨大感染力。因此在战争和训练的空闲时间,他也常找些文学作品阅读,从中获取精神力量。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热爱文学的首长,遗憾的是,他不久被调到军部,我也复员返乡。
我以为今后再也见不到王师长了。1972年春天,我出差路过部队移防的驻地云南开远,顺便去看望战友,住在招待所里。一天,我路过操场,见王师长独自在操场散步,便向他走去,想向他行个军礼,但又担心他不认识我了,毕竟我退伍已多年。正在犹豫时,他却一声喊出了我的名字:“李耀国”,这使我十分感动。王师长首先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,作家冯牧也住在这里,他想介绍我们认识,想让我得到一位文学前辈的帮助。其实我和冯牧早就有联系,冯牧曾是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,培养了许多作家。我的处女作《我和班长》发表后,他给我写信称赞这部作品,并告诫我:“要想成为一个作家,首先必须当好一个战士。”以后每当我有作品问世,他都会来信鼓励。遗憾的是,冯牧当时下部队采访去了,失去了见面的机会。而王争和冯牧的友谊深厚,在我后来到北京看望冯牧时,他都感慨地说:“这样一个军事主官,能够这么重视文学、爱护作家,实在难得。”
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到重庆时对我说:“有一次,我到前线采访王争,见他枕边放着小说《暴风骤雨》,我很惊讶,在战斗激烈的火线上,这样一位身负重任的将军还不忘文学,只能说明他的从容、镇定、胸有成竹。”我相信,经过多年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,这支部队在实战中一定能够发挥其优势,我完全能够想象出王争将军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身影。这样一位善战又热爱文学的军事指挥员,作家当然愿意和他交朋友。至今在他家客厅里,还挂着冯牧赠送他的墨宝:天地有正气,人间贵书香。
1986年,王争从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离休,但他不愿闲着,又开始上老年大学。他说很想把自己的戎马生涯写出来,但苦于写作水平不够。通过六年在老年大学的刻苦学习,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,提高了文学修养,他终于完成了这部《戎马生涯》,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,谨以此文怀念我的老首长王争。
(作者于1961年应征入伍,曾是昆明军区炮兵三二0团战士、陆军四十师政治部专业文艺创作人员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编剧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