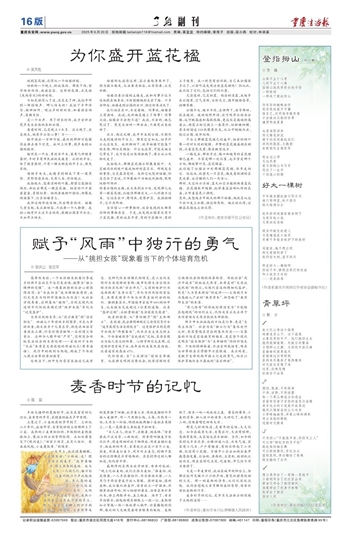◎ 陈 奕
丰收与播种的夏收时节,我坐在窗前回忆过往,麦香里的岁月,在键盘的敲击声中重现。
立夏过了,小麦收获的季节到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读中学,家里较好的土块都种上了小麦。成熟的小麦黄灿灿的,齐刷刷的麦穗挺拔向上,像站立的士兵等待检阅。正如白居易笔下《观刈麦》: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的场景。
一天早上,我还揉着睡眼,父亲便发话:“小林娃,走!跟老汉去割麦子。”我拿着镰刀,跟父亲来到麦地。我与父亲,一人割几行,镰刀划过麦秆的沙沙声此起彼伏,齐人高的麦子,一会儿就放倒一大片。太阳高照,汗水湿透了衣衫,成熟小麦的麦芒沾在我汗湿的手上、脸上,麦茬扎在脚上的口子刺痒难忍。休息时,父亲用带来的篾条捆了四捆,我学着父亲,将挑麦捆的竹竿插入麦捆中,用一只肩膀扛起,立高,压低另一端,又用力一斜插,稳稳地把两捆小麦担在肩膀上,一晃一晃跟着父亲把麦子担回家。
“幺儿幺儿,快放下,去歇着,妈来晒。”母亲看我汗流浃背,心疼地说。母亲将四捆麦子依次打开,将麦穗相对放于晒坝后,用连盖翻打麦子,收成好的年月,家里能打出五六百斤小麦。割麦,用连盖打麦子,风车吹去麦壳,到晒干装仓的过程都是非常艰难的。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,粒粒皆辛苦。
最期待的是周五放学回家,母亲对我说:“晚上吃扯麦粑,我们去推点麦粉。”推麦粉,就是推磨,一人手扶磨担杆,用力推动石磨,一人用勺子将适量麦子放入磨眼。推好麦粉,揉好麦粑,我往柴灶添麦秆,母亲放上一铲猪油,热锅里滋滋作响,倒入切好的酱菜,油香菜香扑鼻而来,掺上两瓢井水,盖上锅盖。汤开了,母亲手指蘸水,捏起面团在锑瓢上一捻一拉,麦粑便如云絮般一块一块地滑入锅中,白雾腾起的刹那,柴灶的火光映亮着母亲眼角的皱纹。麦粑好了,母亲一碗一碗地端上桌。酱菜的酱香、小麦的清香,融入适口的汤香,太好吃了,我连吃三碗,还咂着嘴巴回味无穷。
那是儿时的味道,是童年的美味,久久怀念。如今在城里生活,自驾出行,生活有保障,患病有医保,大家庭也其乐融融。当然,如今的农村也丰衣足食,公路四通八达,水电气通,家家有小汽车,户户有楼房,有的还修起了小洋楼,院前有小花园。乡镇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,打谷机、磨面机、豆浆机、收割机应运而生,现在农村吃豆花、吃麦粑,早已经不用石磨推了。
又是一年麦黄时,我站在城市的阳台上,仿佛还能听见镰刀沙沙的声响,看见灶膛里跃动的火光。那一碗麦粑的清香,从记忆深处泛起。我仍会想起父亲弯腰割麦的背影、母亲灶前扯麦粑的巧手。
麦香时节的记忆,是岁月无法抹去的深植于土地的温情……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人民政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