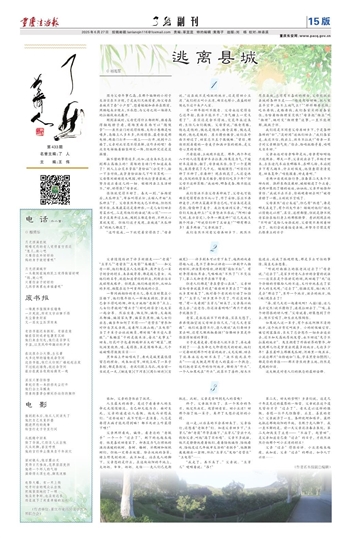◎ 杨旭军
1
因为父母年事已高,在那个偏僻的小村子生活实在不方便,于是我们兄妹商量,给父母在县城买了套“小户型”,想着姐姐和弟弟在跟前,照顾起来方便点,不承想,与父母之间一场持久的拉锯战由此展开。
刚到县城时,父母觉得什么都新鲜,楼房高得翻起脖子看,商场里面东西可以“随便拿”——虽然出门时还得结账,大街小巷都是吆喝声,马路上人多车多,热闹得很,最奇怪是那电梯,两扇门打开——闭上——打开,就到十二楼了,父亲对此百思不得其解,这咋弄的哩?每次坐电梯偏着脑袋研究一阵,但他终究还是没搞懂。
搞不懂的事情还多,比如,这自来水怎么流到那么高楼上的?商场的自动门咋知道我来了?别人上公交车拿张“身份证”(公交卡),按一下当付钱,我拿身份证按几下咋不算呢……父母像刘姥姥进大观园,好奇地打量着县城,并努力适应着这儿的一切。姐姐问县上生活好不,“好,好得很!”母亲说。
很快就觉得不好了。春天一到,“谷雨前后,点瓜种豆”,布谷叫得正忙,庄稼人开始“点瓜种豆”了。父母虽然年纪大已不种地,但仍然闲不住,瓜果蔬菜还是要种些,一是儿女们回去有菜水吃,二是用他们的话说“改心慌”——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,闻到土都是香的,不种点心里就发慌。但他们这才发现,县城连“点瓜种豆”的地儿都没了。
“这咋能成,一下就觉着穷得很了。”母亲说,“这县城不是咱蹴的地方,还是得回小庄湾。”我们村庄叫小庄湾,确实也够小,鼎盛的时候也不过十来户人家。
有一种年轻叫不服老。父母永远觉得自己还年轻,农活不能不干,“力气睡上一觉又有了”。其实还是舍不得地,灾荒年辰过来的,生怕儿女们挨饿。父母常说,“粮仓有粮,饱也是饱的,饿也是饱的;粮仓没粮,饿也是饿的,饱也是饿的。屋头攒些粮食,娃们在外面不好过了,回家总不至于挨饿嘛。”曾经,那快顶到房檐的一仓麦子和满口袋的胡麻,是父母心里的安稳。
只要能动,土地绝不能荒。那年,两个年近八十的人还驾着驴车去拉粪,结果没力气,下坡时车没搡住,翻了,母亲被压伤,住了一个星期院,医药费花了几千元。姐姐埋怨:“叫你们不种了不种了,非要种!现在钱花了,人还受疼痛,住院的钱拿来买粮食,够你们吃多少年!”但父母不这样算账:“我娃哟,哪各是各,账不能这样算!”
我们坚决不准父母再种地了,父母也可能确实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,作了妥协,答应不再种麦子,只种点菜蔬洋芋自己吃,可后来还是没忍住,偷偷种了麦子。我打电话问父亲,“听说你们又把麦种上?”父亲坚决不承认:“阿咧(语气词,表示否定),今年一颗没种!”过几天我又换个问法:“听说你们种了五亩麦?”“哪有那么多!最多两亩。”父亲就招了。
我们自然不同意父母再回乡下。既然不愿在县城,总得有不喜欢的理由,父母能挑出县城的各种不是——“楼房有啥好嘛,把人架在半空中,接不上地气么!”“样样都要花钱,吃水要钱,走路要钱,我们各家买的房各家住,为啥着给物理家交钱!”母亲把“物业”叫“物理”,她对交“物理费”这事,一直不能理解,耿耿于怀。
我们还是不同意父母再回乡下,于是各种各样的“忙”,“没时间”送他们回去。“我们各家走,我还不信,钱出上,班车不拉我!”母亲一辈子对父亲颐指气使:“你去,给咱把路寻着,咱明天坐车回。”
父亲永远对母亲唯命是从,母亲有吩咐他只能照办。那天一早,父亲就出去了,半晌才回来,去长途汽车站坐哪路车,在哪儿转,车站到乡下有几趟车,什么时候发,他侦查得清清楚楚,回来复命:“咱能摸着,好走着咧。”
老两口连夜收拾行李,准备第二天来个不辞而别。孰料东西没藏好,被姐姐逮了个正着,老两口像犯了错的娃娃,讪讪地,父亲开始推卸责任:“我说不去不去,你妈硬要回去咧!”被母亲瞪了一眼,立刻就不言喘了。
父母虽然“逃亡未遂”,但已有“犯意”,要是哪天真走了,有个闪失咋办?姐姐对他们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”,其实,道理都懂,但就是挣不脱老家拴在他们身上的那根脐带。意识到现在的“不听话”是给儿女添乱时,父母便不再闹着回去了。他们尝试着接受县城,并努力习惯没有扎根黄土的日子
2
父亲慢慢结识了许多新朋友——“老蔺”“豆芽儿”“老营长”“王电影”“朱骟匠”……和父母一样,他们都是在人生的暮年,离开自己一辈子刨食的村庄,来县城寄居,都是投儿靠女。从他们的名号,就能知道曾经的职业,判断出往日或辉煌或艰辛。但现在,他们殊途同归,从四山的乡间,相聚在这个叫重邦尚城的小区。
一帮同病相怜的老头儿,每天准时聚在小区楼下,他们像年轻人一样相互调侃,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烟,却大方地给“老联手”点上,儿女们孝敬的“嘴头子”(好吃的零食)也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坐着,晒太阳,谝传,天南地北都谝,谝国家大事,谝家长里短,谝儿女们出息,谝当年如何了不得——“老营长”曾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,追着阿三满山跑;“王电影”当了半辈子公社放映员,那时候“希不受人尊敬”;“朱骟匠”干的是技术活,每次“走事主”回来,灯花叶子包着俩鹅卵石大的“硬菜”,埋炕洞里烧熟,噫,美得很,虽是困难年成,几个娃被喂得敦敦实实……
黑爷庙上开始唱戏了,看戏是城里最值得留恋的理由。戏来如过节,田坎上吼了一辈子秦腔,都是秦腔迷。老汉们提上马扎,戏台前一坐就是一天,《铡美案》《下河东》《周仁回府》《窦娥冤》……许多剧本可以背下来了,越熟的戏看得越入迷,免不了要加以评论——评剧中人物的好坏,评演员的唱功,评剧团“箱红不红”。有时争得面红耳赤,气咻咻地“不然了”(不交往了),第二天却老早在楼下等着。
但老人们都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父亲回家给母亲说最多的是“谁谁回乡里去了”“谁谁从乡里回来了”,他对每个老汉的行动了如指掌:“‘豆芽儿’回乡里半个月了,咋还没回来哩。”有一天看到“豆芽儿”回来了,父亲高兴地迎上去:“这老怂,你还活着咧吗!”两只干瘦的手就握住了。
老家,是永远放不下的牵挂,实在太想了,弟弟便抽空送父母回去住几天,“过几天老家瘾”。他们欢喜得不行,逢人便说“我们要回乡里去咧,还有几颗麻椒要摘!”仿佛回乡里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。
日子走着走着,有些老人就不在了,再也看不到了——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,他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叫老家的地方,义无反顾,回去了就再永远也回不来了。“决不能死在外头”——这大概是所有老人的最后一个执念。他们把老家之外的任何地方,都称为“外头”。一个人如果死在“外头”,就算不了善终,棺木不能进庄,就成了孤魂野鬼,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,简直无法想象。
“听说对面楼上的张老汉过去了?”母亲说。“过去了”,是家乡对老人去世的含蓄的说法——这实在是个很讲究的词,既回避了“死”这个冷酷的字眼给人的不适,又巧妙地表达了家乡人的生死观:“过去了”,轻描淡写,他(她)只是去“那边了”,另外一个地方,该去的地方,他(她)现在去了!
“昂,前几天还一起看戏咧!人猛(猛,这儿表示突然)就不攒劲了,连夜拉回去了。”“唉,真个好得很的好人哩。”父母说着,好像想到了什么,便不言喘了,却生出无限惆怅。
如果说人这一辈子,有个永远纠缠不清的地方,这个地方肯定叫故乡。小的时候嫌它穷,嫌它闭塞落后,长大了总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,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发誓,永不回这“兔子不拉屎的地方”。及至拥有了外面世界的繁华,却发现那儿仍是梦里出现最多的地方,无论多少年!甚至崖畔上那棵龙瓜树,河滩里一块丑石,小溪边那只“白脸媳妇”(鸟,学名黑背白鹡鸰),都是你的牵挂——那片苦焦的黄土地,仍然是灵魂的归宿。
这大概是对老人们的执念的最好诠释。
3
谁知,父亲的身体出了状况。
人生最大的痛苦,莫过于看着亲人的生命之光慢慢暗淡,自己却无能为力。面对生死,父亲的通透让人感慨,他反而安慰我们:“这些娃娃!我不可能一直活着,人总是要得点病才能死得到嘛!都不死世上咋装得下哩!”
父亲照样看戏,谝传,看身边的“老联手”一个一个“过去了”,剩下的也越来越老。他更喜欢回老家了,却再没力气打理他的满沟满坡的桃树、杏树、椿树、洋槐树和核桃树们,但他一定要去坟园,除去坟地的杂草,堵上野兔刨的洞。我不知道,站在先人的脚下,父亲想的是什么,在这块向阳的平地上,太奶奶、爷爷、奶奶、大伯……先人们已先期抵达,此刻,父亲是否听到先人的召唤?
终于,父亲挺不住了,在一个寒冷的冬日,他突然决定,赶紧回老家,回小庄湾!回那个拴了他一辈子、离开了又想扑进怀的小村。
这一走,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了。父亲临行,还想着“老联手”们。知道父亲回乡下,“豆芽儿”和“老蔺”早等在楼下,“豆芽儿”拿出十元钱给父亲,叫他“渴了买水喝”。父亲不多说话,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,看着陪他谝传、陪他看戏、陪他度过几年城市生活的“老联手”,他颤颤巍巍掏出一盒烟,拜托“豆芽儿”发给“老营长”“王电影”……
“我走了,再不来了。”父亲说。“豆芽儿”哽咽着说:“昂!”
第二天,好大的雪啊!乡亲们说,这是几十年没见过的最厚的一场雪。父亲就在这个漫天皆白日子“过去了”,老天是以这样的慷慨,告慰一位平凡但勤劳、正直、善良的老人?父亲跋涉了一生,各种坎坷和艰辛,最终也抵达那块向阳的平地,长眠于先人脚下。我一直不解的是,前一天父亲还准备去医院,第二天却改变了主意——“不治了,赶紧回”。是父亲知道自己要“过去”的日子,才毅然决然扑向那个叫小庄湾的村庄?
父亲“过去”得很安详。小庄湾越来越瘦,我知道,父亲“过去”的那边,如今人丁兴旺……
(作者系本报副总编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