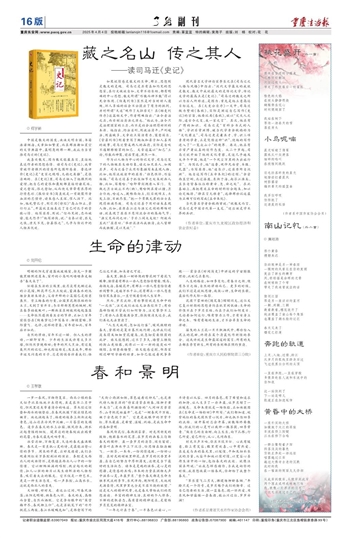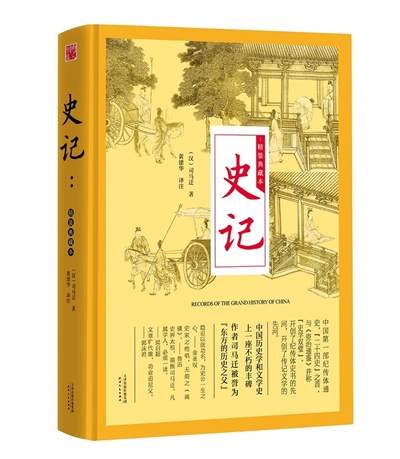◎ 何宇新
中国是散文的国度,泱泱文明古国,书籍浩若烟海,文章灿如繁星,而在那浩瀚如星空的文章典籍中,最明亮的那一颗,我认为当首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
我喜欢散文,因为散文能最真实、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。读司马迁《史记》,我常常被作者强烈的情感所包围所感染。鲁迅评价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,是很准确的。在《史记》里,司马迁融入了他强烈的爱憎,把自己的爱恨和褒贬都直接付诸笔端,爱之愈深,恨之愈切,从而使文章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《报任安书》简直就是一首凝聚作者血泪的悲愤诗,读来感人至深,催人泪下。比如,他礼赞孔子,则引用《诗经》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,开篇就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崇敬心情。他写屈原,则说: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?”他写游侠,说:“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”,几乎与传记中的人物共忧欢。
如果说情感是散文的生命,那么,思想则是散文的灵魂。司马迁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,其行文收放自如,文章不论长短,都有明确的中心思想,散文所谓“形散而神不散”得以充分体现。《伯夷列传》显然是对当时好人遭殃、坏人享福的社会不公提出了有力的批判,并对所谓“天道”观作了大胆否定!在《酷吏列传序》这篇短文中,作者明确指出:“法令者治之具,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”他认为,法令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,而不是社会治理得好坏的本源。他指出,约法省刑,则政治清平;严刑峻法,则盗贼多,文章论点简洁有力,寓意深长。《管晏列传》则着重写了鲍叔和晏子知人善用的故事,司马迁赞美两人的品德,实际是自叹不遇解骖赎罪的知己。文章通篇以“知己”立论,形散而神聚,前后贯通,浑然一体。
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,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极其生动形象,读之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。司马迁善于采用形象描写来表现人物,比如,他写流放途中的屈原: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”司马迁还善于抓住细节之处来刻画人物,比如,写樊哙:“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(纳),樊哙侧其盾以撞,卫士仆地,哙遂入,披帷西向立,瞋目视项王,头发上指,目眦尽裂。”把一个勇敢无畏的壮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司马迁还善于用对话来表现人物,比如,屈原在江边与渔父之间的那场对话,就表现了屈原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:“渔父见而问之曰:‘子非三闾大夫欤?何故而至此?’屈原曰:‘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’。”
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在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中指出:“汉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散文,散文中成就最大的是传记文学,传记文学的最高点是《史记》。”司马迁的散文之所以为后人所称道,是因为:首先是他立意高远目标远大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一文中,司马迁极力赞颂《春秋》,实际是阐述自己写作《史记》的宗旨,他要比肩《春秋》,欲以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其次,他具有广博的知识。司马迁是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”,学识非常渊博,被当代学者余秋雨称为“文化君主”,司马迁更是兼具才、学、识三项素质的学者,正是凭借这种“识”,使他的写作进入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境界。再次,他具有非常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。从二十岁起,司马迁就开始了他的文化考察,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,他是“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”。为写孔子,他“适鲁,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”;为写屈原,他“适长沙,过屈原所自沉渊”。他自述写作《五帝本纪》的过程:“余尝西至空峒,北过涿鹿,东渐于海,南浮江淮矣,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”。在此基础上,再把有关五帝的材料综合起来,加以论定编排,“择其言尤雅者”,选择那些记述最为正确可信的写成《五帝本纪》。
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:“就散文而言,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。”这应该是学术界的共识。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)